富阳学者潜心研究《富春山居图》,出版学术专著及随笔合集
“画里人家”揭秘“富春山居”
文化人蒋金乐的家,安在了好地方,推窗相望富春江。
所以,他有一方印,刻着“大痴画里人家”。“大痴”指的是黄公望的号;“画”,当然就是《富春山居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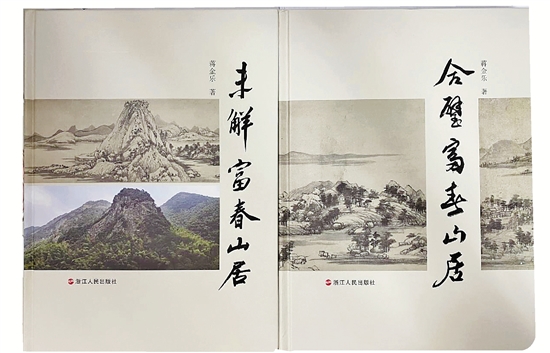
《未解富春山居》《合璧富春山居》书影。
蒋金乐住在江边15年,还是黄公望研究会会长。要说缘分,他觉得身为一个好文化的“老富阳”,如若不研究透了“大痴”和“画”,恐怕枉为“画里人家”。
要说责任,他2010年动了念头时,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举行的记者会上,正借《富春山居图》,道出了华夏文明的两岸连心。因机缘巧合,一张图经火劫烧成两段,前段“剩山图”在浙江省博物馆,后段“无用师卷”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一句“画是如此,人何以堪”,字字沧桑。
经过十多年的研究和走访,他的《未解富春山居》和《合璧富春山居》近日付梓出版。一册重学术研究,一册重两岸文化大家的交流故事,为读者提供不同“口味”的精神食粮:有人偏爱把画中轶事问个究竟,有人感慨画外余音绕梁。
画中究竟有几个人?
文化人的乐趣,也不一定都是板起面孔,追究那些严肃的学术问题。《富春山居图》到底有几个画中人——对于这个视觉“游戏”,他们也乐此不疲。
2011年海峡两岸的《富春山居图》合璧前夕,学者蒋勋在一场关于《富春山居图》的专题讲座中,言之凿凿地说画上有7个人,能指认出来,老师李霖灿才给他满分。
可能是口误,也可能是蒋勋重新数了人数。又过了几年,他在另一次讲座中“纠正”说画里有8个人。很长时间里,8个人也是个共识数字。
2017年,画家、作家刘墉来浙江美术馆办画展,专程到富阳黄公望纪念馆和隐居地参观。他的展品中,恰有一幅亲临的《富春山居图》。那天,刘墉特意问了接待人蒋金乐:画中有几人?
“我们都认为画中有9个人。只是刘墉认为的第九人在桥上,形貌更像是树枝下垂。要说是人,头大身小,比例失调。我认为的第九人,在这里——”
摊开《富春山居图》折页长卷,蒋金乐指着画中前段某一个点,有个隐隐约约像被磨损的痕迹。现存有名的各朝画作临本几十个。为了辨清,他在沈周、董其昌和张宏三位更接近黄公望年代的明朝人临本上,都发现同一个地方有个清晰的人形。
尤其是张宏临本的跋文,笃定了他的想法。“沈周、董其昌的临本上有刘墉所指第九人。但它俩一个是凭记忆画的‘意临本’,一个是后人临的董其昌的临本,准确度都不高。张宏的跋文上则说是‘得遇吴氏亦政堂中,把玩之际,炫目醉心,不揣笔拙,漫摹一通’。吴氏亦政堂正是火烧画作的吴洪裕的家。根据题跋时间,临画的第二年,《富春山居图》即被火焚。”
蒋金乐把这一发现写进书里。这也是两册书中最后写成的一篇文章。
为什么一定要追究画中人?也许,他们也想走进画中,循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隐逸的人生而去。
黄公望生于南宋末年,经历国破家亡,壮年为官却受连累入狱,晚年竟又能潇洒地重拾画笔潜心学习,用时数年完成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件、也是最伟大的作品《富春山居图》。
如此一来,江上垂钓的渔翁、山间茅亭里的读书人、山道上的樵夫……画中这些中华传统文人隐逸时的代号,无不诉说了黄公望“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豁达。而在当今纷乱变化的社会中保持沉着淡定更加不易。
蒋金乐倒觉得,其实无论8个人还是9个人,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去解读。“黄公望画《富春山居图》花了4到7年时间,画画停停。有可能一年前遇到的渔夫移动了位置,成为了两年后再拾笔时遇见的樵夫。也有可能,画中根本就是黄公望一人行走在富春山水间。”
“富春疑案”是乾隆的错?
做研究是件辛苦的“差事”,需要一个接一个的兴奋点来维持。“找出画中人是小‘兴奋’。更大的‘兴奋’是考据了乾隆在‘子明卷’上的54则题跋。”对于蒋金乐来说,这是完成了前辈未竟的事。
在《富春山居图》的研究领域,已故权威、美术史论家王伯敏曾送《山水画纵横谈》一书给蒋金乐。书中有专门的一文讲述他的“富春江情”。“王老偏爱《富春山居图》。为了研究好,还临写了这卷画。遗憾的是,除了认真细读藏在浙江省博物馆的‘剩山图’,在台北的部分至今无法见到。”蒋金乐还记得,赠书那天,王伯敏曾表达希望有人能有机会弄清“子明卷”上乾隆的所有题跋。
“子明卷”便是乾隆“富春疑案”的主角之一。坊间常常视乾隆误把真迹“无用师卷”当假画,反而在假画“子明卷”上疯狂题字这件事为笑话。而当把“子明卷”上所有题跋逐条解读后,蒋金乐意识到,乾隆可能是替大臣们“背锅”了。
乾隆第十四次题跋清楚记录了真假《富春山居图》的辨认过程。
大意是,有一年,乾隆偶得“子明卷”,得知大臣沈德潜曾看到过《富春山居图》真迹,便请他来辨认。沈德潜看后认为“子明卷”是假,因为题跋和他所见的对不上号。此时乾隆没有下结论。
第二年,乾隆又得到一幅“无用师卷”,惊觉更像是真迹,并且题跋与沈德潜所说的一样。因为一时也无法确认,乾隆赶忙找梁诗正等大臣来鉴定。结果,大臣们告诉乾隆,前一次得到的“子明卷”才是真迹。
于是,乾隆在题跋中感叹:“灯下骇以为更得《富春》者,乃误也。”意思是,原来当初以为“无用师卷”更像真迹,是自己判断错了呀!
“子明卷”确是佳作。蒋金乐在查阅资料时发现,书画家启功曾研究认为,这是清朝最有代表性的画家之一王翚的临本。也难怪得到“子明卷”的时候,乾隆就爱不释手地题跋了数次。
然而,一众大臣们真的没看出真假吗?还是他们集体说了假话,为讨乾隆欢心?如果大臣们驳了乾隆面子,龙颜会大怒吗?
在蒋金乐看来,乾隆并非一个“知错不改”的人。
“子明卷”在乾隆身边54年,平均一年题一次,随身出行,如同护身之宝。在乾隆的第二十八次题跋中提到,他在落脚天津盘山一带静寄山庄时,又想到了富春山水,并联想到了韩愈名篇《送李愿归盘谷序》。这是乾隆误把河南盘谷,当作天津盘山了。
“后来,乾隆发现自己搞错了地方,还特意写了一篇《济源盘谷考证》,并制摩崖立在盘谷和盘山两处,检讨自己不求甚解的行为。”蒋金乐专门找来了《济源盘谷考证》的内容附在书中,佐证乾隆的雅量。
蒋金乐常常想,或许当年,时年不过三十五六岁、艺术造诣不深的乾隆是真心请教大臣们的鉴定结果,奈何大臣们估摸错了圣意;也或许等乾隆更成熟时,如果能再多看一眼“无用师卷”,就能发现自己的错误吧。
然而,阴差阳错反而应了道家“祸福相依”的说法。
黄公望晚年入全真教修道,度过了几年为人卜卦的生涯。冥冥之中,老人像是为《富春山居图》卜了一卦——
乾隆冷落真迹,题跋赝品,成就了两幅佳作。真迹也得以静静妥善保管在清宫200多年,免于流落民间遭遇“巧取豪夺”。
而今,《富春山居图》因为遭火焚而被分为两段,分藏于海峡两岸,以一幅画暗喻着团圆的期盼。
“当年沈周曾拥有一段时间《富春山居图》,后来被盗。多年后意外在朋友家中再见时,他在画上潇洒题跋‘翁在仙之灵……择人而阴授之耶’。大概是他认为,按照自己随和敦厚的性格,怕是护不住这幅绝世之画。”蒋金乐感叹,“这么看来,黄公望确实一直在为《富春山居图》选人呐!”
“痴翁真本”全然在富阳?
多少年来,《富春山居图》“画中兰亭”的风采,勾引着文人墨客赶来一睹“痴翁真本”。
蒋金乐在每一次参与活动或接待宾客后,就写一篇小文作记录,最终编成《合璧富春山居》一书。时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书画家罗永贵、文化研究学者李欧梵、诗人郑愁予、影星刘德华……一众人中,著名鉴定家、艺术史学界泰斗傅申最让他动容。
“真的有人视《富春山居图》如信仰虔诚对待!”蒋金乐记得,那年,傅申不顾78岁高龄,执意爬上庙山坞去黄公望墓地祭拜(此处虽是没有墓碑的疑冢,但有富阳县志、《浙江通志》记载说是黄公望墓,考古也认定其建于元明时期,而江苏常熟所谓黄公望墓并无文献支持)。临下山时,他突然回头,用双手围住嘴做喇叭状,如顽童一般向着墓地方向大叫道:“大痴先生我们下山了,再见!”
那次相会,傅申自述,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曾租一辆摩托车跑在富春江两岸找寻画中景,可惜一无所获。于是,当蒋金乐展开一张几乎“复刻”《富春山居图》的摄影长卷时,这位虔诚的“教徒”怔住了。
事后,傅申向蒋金乐讨要了一份《富春山居图》实景地摄影卷,并题跋称,原本并不能理解画中为什么卷尾突然有孤峰突起,见了照片“方始恍然……昔见王伯敏先生以照片剪贴拼凑,亦无此佳妙也”。
《富春山居图》是写生还是写意?如果是写生,有没有对应的实景?如果有实景,地方在哪儿?许多年来,种种问题皆有争议。
蒋金乐一直坚定地认为,《富春山居图》有实景,画的就是富阳。这幅长卷便是2012年由他沿着富春江富阳段的中埠大桥到新沙岛约30里长水段拍的7张照片拼成的。
据王伯敏在《山水画纵横谈》记叙,他早年曾徜徉在富春江数百里察看,认为《富春山居图》“所画富春江的两岸,有可能起自富阳城的株林坞、庙山坞一带……它的起手与桐庐无关,它的结尾与钱塘江也无关”。
“王老也在富阳拍摄过数百张照片,拼凑成一幅‘富春山水摄影剪贴图’。但他的元素细碎。我的摄影只有7张照片,进一步证明‘痴翁真本’在富阳。”蒋金乐说。
大约是觉得能够入画而居是最大的幸福吧。2022年春节,傅申搬来富阳黄公望村定居。有人虽无法“入画”,却把情感托物吟唱。
而今,在富阳黄公望纪念馆北面的香樟树下,有一块长条形的石碑,上面刻着一首长诗——《富春山居图的涅槃》:
“山,一直蹲在历史的熊熊大火中发呆,守望着岁月日渐荒寒;而水,早已离我们远去,寻找它的故乡……”
这是蒋金乐请台湾著名诗人“诗魔”洛夫在参观黄公望隐居地后,专门创作的诗篇。石碑上的书法,也是诗人亲书的。可惜2019年诗碑落成前,洛夫已经仙逝。
幸好还有诗人那端庄内敛、和“诗魔”形象判若两人的书法,终于留在了《富春山居图》的实景地,沉沉地吟诵着故土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