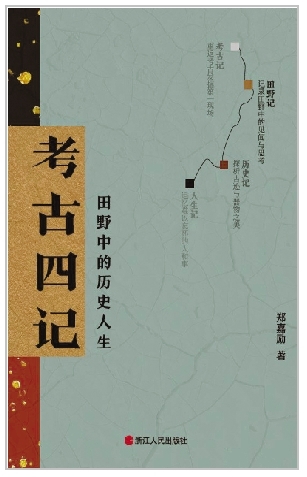
| 关注 | 《考古四记》 郑嘉励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4年3月 ——读郑嘉励新书《考古四记》 最近在读郑嘉励老师的新书《考古四记》。说来,书中大多数文章,我很早之前读过。现在重读,随便翻到一页,也依然是津津有味,手不释卷。 好的文字,就是这样。 1 《考古四记》很好读,在于它不是枯燥的学术著作,也不是虚构类的文艺小说。郑老师自己说是“杂文”,因文体和趣味比较杂。他说自己写作态度是认真的,既不随便,也不散漫,所以不愿意称其为“随笔”或“散文”。我倒是觉得,这才是气味纯正的随笔。有趣的人,写有料的文章,也只有随笔能承载这样的内容。 认识郑老师很多年了,至少十五年——认识时,他就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在漫长的时间里读他的文章,从报纸专栏读到一本本的书,眼见得风格一年一年有小小的变化。文字藏不住一个人的性情,尤其是非虚构文字,作者用文字一点一点构建他的世界、他所生活的时代,经年累月,极富耐心,使之越来越饱满丰富。这有点像是考古工作。考古是把过去的时光,像拼图一样慢慢拼出来,所依据的材料是那些光阴的物质碎片,如海浪推到沙滩上的贝壳一样。这件事,同样需要巨大的耐心,需要等待机缘。 写作与考古,一个是面向未来,一个是面向过去,而所做的工作,居然如此相似。 2 与郑老师聊天,他常随口说出一些很幽默的话来。说的时候,自己并不发笑,而是一本正经。这种情形,也在他的文字里时常可见。 《樊岭》中,他说到1934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到宣平县(今浙江武义县)调查元代建筑延福寺,坐轿子路过武义樊岭村。写到此,他话题一转,说梁思成多年前的学术著作一再重版,“今天的人们,说起梁思成,就想到林徽因,继而便是‘人间四月天’‘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之类的掌故。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要记住,他们夫妻俩的主要成就,并不在于鸳鸯蝴蝶。” 郑老师这个时候,就调皮起来,打趣了一把“文艺青年病”——“文艺青年炒热了很多地方,也糟蹋了很多地方,糟蹋了云南丽江,再来糟蹋浙江乌镇。这叫作‘依次糟蹋’。” 因为和郑老师熟悉,读这些文字,眼前会浮现他说话时一本正经的神情,叫人忍俊不禁。 郑老师因为工作的缘故,经常跟坟墓打交道,自然对坟墓有深入见解。他的上一本书是《读墓》,也是相当畅销,好评不断(我有点奇怪,这样的书普通读者会作为深夜枕边读物吗);他的著作《南宋墓葬研究》《丽水宋元墓志集录》,则是学术本业(我也暗自想,他所见过的墓,自然都已融入他的精神世界,构成他世界观的一部分,而他看人情世味,是不是也有一点墓眼观世的味道)。 “我不能理解的是,今天有人居然会把盗墓者描述成身怀绝技的高人。其实,发掘砖室墓本质上是种体力活,略带经验活的成分,钢筋入土,遇到砖头,死活钻不下去,这也用不到太多的生活经验。”他还说,“我认为,盗墓够不上手艺活的标准。” “我在龟山的工作收获,除了调查乌牛溪流域青瓷窑址群和获取大量瓷器标本上,就是终于读懂了温州的椅子坟——自古及今,人类以最大的激情从事各种劳动,只为换取内心的充实,以抵抗宿命的悲凉。做点事情,有个念想,找个寄托,椅子坟如此,考古工作亦如此。” “‘意义’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只能依靠自己去寻找、去定义、去创造。我们每天都在努力赋予世间万物以各种各样的意义,当我能够这么想,人生容易多了。” 若干年前,郑老师因为一句“上班就是上坟”走红网络。不正是如此吗?坟上得多了,看什么事情都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郑老师时常有这样的通透之语。既冷峻,又俏皮。 3 和郑嘉励老师最近一次碰面,是在黄岩。一行人走到西江闸附近,郑老师随口就给我们介绍起此水闸的历史。 西江闸设计和主持修建者,是中国著名的水利专家胡步川先生。水闸建成于1933年,南迎西江水,北挡永宁江水,起到泄洪排涝的功能。在当时的技术条件和经济环境下,成功完成这样的大型工程,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西江闸作为重要水利设施留存至今,也成为了重要的历史文物。 与学识渊博而又有趣的人同行,哪怕是短短一小段的散步旅程,都是一件快乐的事。看过了西江闸,郑老师顺便就把我们带到了一座纪念碑前。此时夜已深沉,林中黝黑,几个人打着手机的电筒光,读清了碑上的大字:“魂兮归来”。 郑老师说,当年建造西江闸时,占用了一块坟地,这块碑正是胡先生为那些无主孤坟而立的,字也是胡先生自己写的。“多么有人情味啊!”郑老师说。 《考古四记》这本书,正因郑老师有深厚的学术背景,写来又举重若轻,出入自由,读来便好似春行山野,一路繁花。专业学者的视角,提供的内容是扎扎实实的干货,获得新知也获得趣味。 如《唐宋时期的西湖摩崖题刻》一文,郑老师写道西湖诸山摩崖题刻的分布,做了细致且详尽的整理。其中写到一例,熙宁六年(1073)七月,王廷老携部属游览烟霞诸洞,分别题名于石屋洞、水乐洞、烟霞洞。在此几个月前,杭州知州陈襄、通判苏轼等人,亦在石屋洞有题刻:“陈襄、苏颂、孙奕、黄颢、曾孝章、苏轼同游。熙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在这里,郑老师有一句感叹:“有趣的是,杭州刺史陈襄、通判苏轼与两浙转运使王廷老同为地方官,但州衙和转运使衙职责有异,结伴出游的朋友圈竟然完全不同。” 文章的有趣,有时候就是作者心态松弛的呈现。这么一个闲笔荡开,读者便会心一笑。 4 此书读来,颇有许多这样的会心之处。而会心何来?是作者怀抱这样的真诚之心,这也是本书的珍贵之处。 述及自己1995年进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为职业的考古工作者,直至今天。当时他也有两种准备,不能进考古所,就回老家给领导当秘书。郑老师说,“如果我走了‘从政’的道路,当不当官不知道,也许不会像现在这样的胡说八道。人生,是刹那的因缘际会。” 说到考古工作的辛苦,他也是把自己想法和盘托出——“从不觉得考古工作有多苦。而今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事务烦冗,又要东奔西跑,才感觉工作辛苦、人生辛苦——这也算‘中年危机’的一种吧,曾经信奉的价值、意义,面临重新洗牌——这不是考古人特有的精神危机,任何职业、任何人都要面对,如果对事业并不真正出于热爱,始终保持激情,绝非易事。” 诸位,一位用文字与读者交流的写作者,不管他是不是专业的学者、专家,愿意把他的内心敞开来,这是文字动人的原因。在一个发朋友圈都想把自己隐藏起来的年代,郑老师这样的专业学者,愿意坐下来,耐心地跟人聊聊天,把自己的内心世界、人生经验、工作得失坦承给你,这是非常难得的事情了。很多时候,不愿说,不必说,不想说,为啥要说——所以,我们真应该珍惜郑老师,赤诚如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