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城地铁公共艺术《莲响节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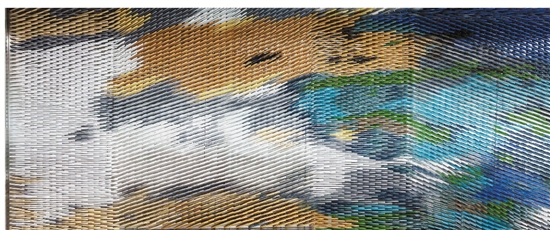
杭城地铁公共艺术《钱江潮涌》
你见过有生命的城市吗?
当然不是那种建筑千篇一律,人们的脸上、心里因为充斥着后工业化时代的焦虑和复杂,而蒙上了一层灰扑扑颜色的城市,也不是那种结构散乱无序、基础设施陈旧、日益被边缘化的城市。前者太过紧绷,环顾四周很难寻得认同感,而后者略显单薄,身处其中缺乏获得感。
我所说的,是像卡夫卡的布拉格、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普鲁斯特的巴黎、博尔赫斯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那样,有血肉,有呼吸,有起伏兴衰的“看得见的城市”,是像2010年上海世博会城市生命馆那样,有活力、有循环、有生活、有故事的“吐故纳新之城”。
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一位踏浪而来、风尘仆仆的旅人,怀着虔诚之心涉水上岸,触摸蜿蜒曲折的海岸线和波涛起伏的心跳,轻叩城门。那一刻,好像人类基因中里一个细微又重大的秘密被揭开了,关于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的答案,在我们与城市的对话中,渐渐显影。
“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早在1949年,毛泽东同志这样号召全党。此后中央先后召开3次城市工作会议,研究解决城市发展的重大问题。从1978年到2014年,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城镇常住人口由1.7亿人增加到7.5亿人,城市数量由193个增加到653个。数据变化的轨迹,从一个侧面描绘出一个农耕古国向着城镇化、现代化不断迈进的精彩画卷。实践充分证明,城市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建设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
一座城,像一个人。作为一个有机生命体,牵一发而动全身:命脉系统缠绕产业和能源的根基,因群而兴;消化系统勾连人流、物流、车流、云流,互联互通;神经系统规划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上层建筑,千头万绪;肌理系统,打造划分有序的建筑和街区,展现各个历史年代的生态风貌;灵魂系统则以山峦、河流、湖泊,节日、老街、古寺,存放悠长的文化记忆,代言独特的精神品格。
从上海世博会城市生命馆那个建成于1900年、见证钢铁时代诞生的巴黎里昂火车站,到指向未来的智慧城市,步行不过几分钟,却像进入了一段时光隧道;我们正是在这些日日相望的城市景观中生活、劳作与休闲,构建对自身身份的认知,完成自我塑造和演化,并在群聚中找寻精神符码和心灵认同;而最后通过的环形银幕讲述的“广场故事”,既似预言也像隐喻:对作为人类栖居生息之所的“家园”,及对城市战略性空间及其因生态链集群而生的“流程”,应有更深入的规划和设计,相应地,城市化建设推进过程中所产生的城市建造和产业结构上的单一化、同质化问题,值得警惕和反思。
但城市问题往往很难“被预见”。更何况,眼下中国经历的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每一年,全世界40%的混凝土倾倒在这片东方的土地上,一座座为汽车设计的新城新区拔地而起,一个个摩天大厦的楼高纪录被不断刷新,一块块水网被填平、修筑道路,继而层层铺设高架的背后,是人的素质和需求的提高。
“不同人群、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交融,呼唤多目标的发展、多元化的生成、多样性的满足。”在上海世博会世博主题馆城市生命馆总策划、中国美院院长许江看来,政府、社会、市民作为城市的主体,构成了一个以“我们”相称的“城群体”。千万人的城市,就有千万个故事,汇合、交融、盘旋、上升,转化为空气和氛围,才能被称为城之品格、城的精神、城之秘钥:“‘建造公共’的命题,在于促进城市的共同进化,需要更多设计人力和文化人力的投入。”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所著的《伊斯坦布尔》,副标题叫“一座城市的记忆”。在他的笔下,故乡是一座充满“呼愁”( 土耳其语“忧伤”的意思)和帝国遗迹的老城,早已渗入少年帕慕克的身体和灵魂之中,他的内心总有一台机器,强迫他阅读在街上看到的每一个字。“阿卡班银行清晨肉饼店织物保险”、“在此饮用日用肥皂理想时光珠宝”、“努瑞巴雅律师分期付款”……这些看似无意义的表述、意象的随意堆砌,却能拼接、串联起一座城市的风貌。
更不思议的是,随着他的叙述,我们的眼前仿佛也“走”来一台机器,绿色的钢铁外壳,烧柴油的内核,巨大的铁钉将它们镶嵌在一起,喷着蒸汽,仪表乱颤,嘎吱嘎吱地,仔细听辨,还有几句不成段的伊斯兰歌谣。
原来,城与城、人与人、人与城之间,是可以相互抵达的。


